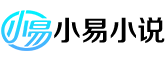一秒记住【笔趣阁小说网 www.biquge34.net】,精彩小说无弹窗免费阅读!
“你说什么?”谭央听了陈叔的话,半天没回过神儿,待明白过来后便手忙脚乱的去开车门。陈叔狠狠抵住车门,“少夫人,你现在去问少爷,他不会承认的,他不让我对你说!”陈叔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,“他在上面看着咱们呢,你先回去,晚上十点以后,小小姐睡了你再来,我给你开门。”
谭央心慌意乱的开车往出走,在街口转弯时差一点儿就撞到了树上。把车停在道旁,谭央失魂落魄的坐在路边,初冬时节,一派萧索,寒风把残枝刮得哗哗直响,更把这份荒凉,演了个生动。
他说他一片真心的爱着她,却依旧果决狠辣的杀了她身边所有至亲至近的人。在他的世界里,爱情可以和一切外物割裂开来,她却做不到,更无法理解。一面是情深似海,一面是仇不戴天,她在这样险峻窘迫的境地里苟且的活着,她愤怒委屈自责无助,若不是尚算得心性坚定,恐怕早就被逼疯逼死了。她凭着一份孤勇,用尽所有气力的往出走,就在眼见得些许希望时,他却用自己固执独断的爱,毁了她所有的退路与出口。
夜深苦寒,陈叔悄无声息的打开了毕公馆的后门,谭央就站在院墙外。陈叔看见谭央身上的薄呢大衣,心有不忍的问,“少夫人,您来了多久了。”“一直没走,”她心不在焉的望着陈叔,淡淡的说。
“他抽了多长时间了?”谭央艰难的问。陈叔叹了口气,“一年多了,从去年秋天知道你病了以后。鸦片这玩意是怎么回事儿,别人不知道,少爷能不清楚吗?所以开始的时候也尽量控制,也想着断,小小姐得肺炎你来照料的那段时间,他抽的最少,我都以为他这就要戒了呢。可你走后,还是不行。若说是真正不管不顾的抽开,还是今年春天的事,我反复问他因为什么,他说他大概没什么机会了,因为仅有的一次机会,也被他错过了。几个月前少爷忽然烟瘾大了起来,那个抽法,不要命了一样,我问不出原因来,可估摸着,你们大概又闹了什么矛盾。”
谭央一声不吭的往前走,看着她的背影,陈叔紧锁着眉头,带着怨气的低声自语,“早知今日,十三年前在同里,那晚上,我就该……”
陈叔把谭央带到楼上的房门前,悄无声息的走了。谭央鼓足勇气才伸手旋开门把手。屋里很暗,只开了盏壁灯,毕庆堂穿了睡衣背对着她,躺在睡榻上。谭央能看见他吐出来的烟雾,形状可怖,仿佛是燃了许久的人膏蜡烛。
毕庆堂听见有人进来,便不耐烦的说,“陈叔,你回去睡觉吧,不用管我!”谭央想开口说话,却发不出声音来。毕庆堂发觉人还没走,不悦的回过头,刚要说话,看见站在门口的谭央,顿时怔住了。少顷,回过味儿来的毕庆堂第一反应竟是把手中的烟枪藏在身后,可是谭央又怎么会看不到。心知肚明的毕庆堂自嘲一笑,起身下了地,谭央站在昏暗的灯光下望着他,眼睛里亮晶晶的,是泪,还有满眼的悲悯与痛楚。
毕庆堂不敢多看,忙移开眼,打起精神笑着戏谑,“小妹,这大晚上的偷偷摸摸的跑进来,是不是一个人睡不着觉,找我解闷儿啊?”说着,他走近了,伸出手就去搂谭央,带着蛊惑的语调,柔声说,“来来,大哥哄你睡,叫你睡到明天中午都下不来床!”
毕庆堂刚把谭央揽到怀里,还不及搂实,却被她伸手推开。谭央用发抖的声音质问他,“你要干什么?鸦片这东西不能碰你不知道吗?”毕庆堂背回手去,事不关己的回答,“玩玩嘛,也不能怎样,你不用操心。”
谭央见他这个态度就急了,“你说的轻松,吸大烟还说是玩!你和你父亲做了那么多年鸦片生意,大烟这东西害过多少人你会不知道?”毕庆堂冷哼一声,“那是别人,我有的是钱,就算是抽到一百岁,也沦落不到卖儿卖女的地步!”“就你这个抽法,还想活到一百岁?”话说出口时,谭央撑不住的哭了出来。
毕庆堂不屑的笑了,低头看着谭央,机械的重复着,“活到一百岁。”“你就戒了吧,趁着时间还短!”谭央看着毕庆堂,眼里转着泪花,恳求他。毕庆堂走了两步,坐到榻上,瞥了一眼烟枪,明显的不耐烦了,“我有分寸,你少来管。女人若是管得宽了,就惹人腻烦了!”谭央见他如此执迷不悟,束手无策之际目光落到了榻上,她失了理智的冲到榻边,看都不看的端起托盘上的烟枪烟灯等一众器具,冲动的喊,“我让你还抽!”说着,来到窗户旁,打开窗子就要往下扔。毕庆堂稍一愣,忽的在后面气急败坏的喝道,“住手!你给我住手!”
谭央被他这一声喊唬了一跳,手上的动作慢了两秒,这时毕庆堂一个箭步冲过来,就在托盘撇下去的那一瞬间,他一把抓起托盘角落的东西,稳稳攥在了手中。虽然颇为仓促,可谭央还是看清了,是戒指,是那年他从香港带回来的那枚钻石戒指,在她手上,戴了整整八年。
多少人期盼能情比金坚,爱比石固,到头来总是一场空,诚然悲哀;而他们,金石宛在,情爱犹存,却再不能相守,这才是悲哀中的悲哀。
谭央无力的瘫坐在窗下的沙发上,上气不接下气的哭了起来,绝望无助。毕庆堂自来是最看不得谭央哭的,她这样哭着,便像是剜着他的心,更何况,谭央此时哭的因由,他懂。毕庆堂迟疑片刻,猛的坐到谭央身边,伸出手将谭央踏踏实实的箍在了怀里,还不待谭央挣扎,他就在她耳边急切而坚定的说,“就一会儿,就一会儿!”
谭央心头一涩,没再动,他身上的体温,呼出的气味,甚至于他穿的睡衣的质地,都是她再熟悉没有的,那都是她平日里不敢直面不愿承认的深深眷恋。毕庆堂看着怀里的谭央,闷声道,“刚刚身上那么凉,还要推开我,不叫我抱!” 语气里有气有怨,更有浸满辛酸的微甜。拥着怀里的谭央,毕庆堂的心中百感交集,酸楚难辨。两个寒暑的光阴,是漫长人生的短短一瞥,却是他平生里,最艰难的两年。
谭央低声哭着,毕庆堂颇为无奈的轻抚她的肩,她的背,手指顺着脊柱两侧轻轻滑过,虎口掠过脊柱,到腰下时,谭央身上不自主的一颤,毕庆堂见状,心头一动,便又将她搂紧了几分,继而缓缓低下头去吻谭央的鬓角。他的嘴唇碰到她时,她忽的止住了哭,稍一愣便扭过头,要从他怀里出来,毕庆堂非但不松手,还凑过去亲她的耳后,压低声音在她耳边柔肠百转的说,“我知道你想。”
谭央听了他的话就怔住了,随即哇的一声大哭起来,一面哭一面任性的摇头。毕庆堂看她如此,心中爱怜起来,才缓缓松开了手,起身拿了手帕递给她,谭央不接,毕庆堂就慢慢的替她擦了眼泪,带着感慨的语气埋怨,“爱哭,还不带手帕,十来年的不长进,”他捏住了手里的手帕,微微叹了口气,“其实我也是认识你后才有了带手帕的习惯的,因我既爱你哭时的狼狈样,又见不得你的眼泪。自打在谭叔叔灵前第一次见你时就是这样,十多年一直如此,也算是怪事一桩了。”
过了一些时候,谭央渐渐收住了哭声,毕庆堂望着她,带着一腔爱意的嘲笑她,“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,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,大烟鬼一样!我就是抽上三十年的大烟,也到不了你这地步!”谭央见他这样说,只好苦口婆心的劝,“你也知道大烟鬼不是什么好话,就不要抽了,你这样,你这样……”她心烦意乱的停住了,掂量了半天才又开口,“囡囡慢慢的懂事了,你这样,她该多难过,多心疼自己的父亲。你也不想叫她有个天天搂着烟枪的大烟鬼爸爸,对吗?我求求你,我替囡囡求求你,戒了吧,你看看女儿啊,你就当是为了女儿,为了女儿还不行吗?”
毕庆堂紧锁着眉头,不愿再听下去,他粗鲁的打断她的话,“为了女儿,自然全是为了囡囡,若不是为了她,你以为我会怕死吗?”听了毕庆堂的话,谭央一动不动的愣在了原地,半天没缓过神儿来……
那个晚上,谭央一直哭着求他,求他戒掉烟瘾,可她实在不知自己该用什么样的立场,该拿什么样的理由去求他,她就这样流着泪苦苦哀求着。倒更是形状堪怜,使人不忍,所以天蒙蒙亮的时候,毕庆堂还是吐口同意了,说自己会戒,叫她放心。之后谭央去言覃的房间躺了两个小时,早上孩子一睁眼就看见妈妈,自是异常开心。
谭央牵着女儿的手下楼时,毕庆堂正在餐桌旁一边抽烟,一边翻着报纸,早餐摆在桌上,种类不算多,却都是家常可口的。吃过饭后,毕庆堂告诉她,车已经叫司机替她发动了。她打开车门时,在这个初冬的寒冷早晨,车子里却暖得一阵热气扑面而来,她知道,他一定叫人用炉子烤过车里了。谭央开车要走时,回头望见女儿站在客厅的落地窗里冲她挥着手,毕庆堂也换好了衣服准备出门办事。
如果,假使,倘若,没有那些事,那么他们毕生的每一天都会像这个早晨一样开始,平淡安稳又温馨。
谭央回到军队医院的上午,从前线回来的徐治中还带回了受了重伤的李副官。李副官要想活命,只有自骨盆以下,截掉双腿。快四十岁的男人了,在剧痛下还挣扎着嚎哭大叫,“别管我,叫我死!叫我死!”徐治中死死抵住他的肩,咬着牙厉声训斥,“为了救你这条命,我带着弟兄们冒着被炸死的危险从地雷区里把你背出来,你想死,对得起我们吗?”可在上司的威严下,头一次,李副官竟是丝毫不怕,“谁要你们救我了!我宁可死,也不做个废人!”
徐治中的神色凝重起来,思忖良久,他方郑重其事的开口,“李哥,你来打仗是想叫一家人过上富足太平的日子,而他们呢,也正在家里等你回去团圆,老太太等你回去陪她看戏,嫂夫人等你回去同她摸牌,孩子也等你接他下学。他们等的是你这个人,哪管只有一口气!而不是一封通报死讯的信。李哥,你的这个团圆美满的家,是多少人朝思暮想而不可得的梦。而且我敢说,只要有这样一个家庭,人在任何时候就不该也不能糟践自己,自暴自弃,”稍喘口气,他又慢慢的补了一句,“因有所望,方得勇力!”
李副官听了徐治中的话便不再挣扎,他依旧是哭,可这泪却是入了心的感怀牵念,又是另一番心境与景象了。徐治中慢慢松开手,坚定的对刘法祖说,“给麻药,手术吧!”
徐治中说,人只要有所指望,才能有勇气与力量,才不会自暴自弃,自我作践。他的这些话,字字如针,刺进谭央的心房,叫她的心忽忽悠悠的抖起来,又闷又痛。
谭央别过头看向窗外,隋婉婷正在外面,呆呆的站在门口,看着来来往往被担架抬进抬出的伤员。这个自小在温室里长大的姑娘,情窦初开便情根深种,可是天不开眼,爱人惨死,她连为他生个孩子这样微末的指望也落空了。半分希望都没有的她如今连精神都不大好了,抓住个人就把章湘生的照片拿出来给人家看,也不管这人认不认识,她前一天和这人说没说过,都要从头到尾的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别人听。
其实这一刻,谭央在心底里是嫉妒隋婉婷的,她爱的人为了救她父亲的命死了,而她爱的人呢?却为了钱要了她表叔,甚至她父亲的命。虽然他们之间的爱比隋婉婷和章湘生要浓厚的多,可即便他抽着大烟,遭着罪,乃至是死了,她也没那个立场与理由为他痴为他疯,为他堂堂正正的抒发出心中的剧痛与悲戚。
徐治中来到谭央身边看见满脸泪水的她,愣住了,这时下属催促他去总司令那里开会。他顺着谭央的目光看见了外面的隋婉婷,之后他又回过头看了眼手术室的门,李副官正在里面接受截肢术。他忽然拽着谭央的手,将她拉到面前,看着谭央的眼睛,徐治中面容坚毅的说,“央央,我一定要打赢这场仗,要尽早结束这一切!这里所有的血泪,都要在侵略者的身上,得到偿还!”说罢,也不等谭央有所反应,他便迈着大步,毅然离开。
李副官的手术做得很成功,刘法祖甚至为他保留到股骨中段。在这场战争中,每天十数台的手术,半年来刘法祖的外科手法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与成熟,一般医生需要四五个小时才做得完的大型手术,刘法祖只用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得干净漂亮,他“沪上第一把刀”的名声自军中传出,蜚声华东,甚至连日本人都有所耳闻。
可是淞沪的战局,却一日千里,无可挽回。日军逼近上海,政府也做出了撤出上海的准备,很多官员的家眷和军需物资都运往了重庆,章湘凝也要随着父亲离开上海。章总长的汽车都开到了军队临时医院的外面,却等不到他的女婿一同离开。战争惨烈,伤者无数,刘法祖的手术已经排到了三天以后。
在两个手术的间隙,穿着手术服,来不及摘手套的刘法祖奔到外面,看着在车里苦苦等候的章湘凝,他一个趔趄,差点儿摔在车前。章湘凝怀孕的月份大了,厚重的大衣都遮不住腰身,她笨拙的去扶刘法祖,不由分说的拽着丈夫的手,“你跟我走,跟我走!”照旧是大小姐似得命令语气,眼泪却不争气的在眼眶里打转。
刘法祖眼眶发红的蹲在章湘凝的面前,“湘凝,我不能现在走,还有那么多伤员等着我做手术,他们刚从前线下来,不立刻手术,运走就会死!”章湘凝哭着哀求,“那么多医生,要别人去做好不好?”刘法祖摇了摇头,握着章湘凝的手,耐心的对她说,“不行,有些手术,只有我能做!”“可是我也只有你啊!我已经没了哥哥,不能再离开你了!”刘法祖点着头,眼泪也直往下掉,“我不离开你,湘凝我不会离开,你先和孩子去安全的地方,我做完这几个手术,迟几天就去找你们!”
章湘凝看着刘法祖,期期艾艾的说,“他们都说,打仗时什么都会发生,过了今天可能就没有明天了,所以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,一刻都不能分开!”刘法祖红着眼眶坚强的点头,“湘凝,我说好了一辈子和你在一起,就不会食言!无论发生了什么,我都会去找你,哪怕有再大的困难,我从上海,走也要走到重庆去!”章湘凝上气不接下气的哭着搂住刘法祖,“好,我信你,我等你!”
临行前,刘法祖揽着章湘凝的腰,在妻子隆起的肚子上,深情一吻。
从这天起,谭央再也无法入眠,闭上眼脑子里就会重现那一幕――她生言覃前,在医院里,毕庆堂扶着她的腰,将头紧紧贴在她肚子上,哑着声音哀求他,“小妹,无论发生什么,都不要离开上海!”
晚上睡不好觉,白天的伤员又多,就在谭央心绪烦乱、精疲力竭之际,这最后一根稻草,还是压了上来。这天早上,忙了大半夜,只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的谭央又进了病房,一个又一个的病床密集的排在一起,病情不太重的伤员三五个围在一起,叽叽咕咕的说着什么,看见谭央进来他们就笑了,一个年纪小的伤兵活泼的冲谭央喊,“徐夫人,恭喜你了?”
大家看谭央一副不明就里的样子,就把手里的报纸塞给她。谭央一看上面的内容,眼前便冒起了金星。她和徐治中这个周末结婚,这件她自己都快忘记的事情,他却登了报纸的头版,张罗得满世界都知道了。他没给自己留任何余地,更没给她留。
愧疚,无望,哀伤,恐惧,种种情绪涌上心头,谭央的心口突突的跳痛,她的肩背控制不住的微微颤抖着,扶着床架缓缓靠在了墙上,谭央的额头上冒起了冷汗。
下午时,林副官来到徐治中的办公室,正看见他焦头烂额的做部署、接电话、签文件。他在旁边等了好一会儿,徐治中这才稍歇片刻,“怎么来我这边了?”“从阵地上下来,送几个重伤员来医院。”徐治中点了点头,示意林副官把门关上,“昨晚军长师长们开会,要升你军阶,这两天就下委任状。”林副官郑重的立正敬了个军礼,“谢师座栽培。”徐治中凄楚一笑,“打着仗,死着人,升着职,这是血淋淋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啊!就是不知道这成千上万的枯骨能不能早点儿换来战争的胜利。”正说着,电话响了,徐治中伸手去拿听筒,匆匆对林副官说了句,“忙你的去吧。”
徐治中接完电话,只见林副官还站着原地,就问,“怎么了?”林副官腼腆的笑了,“看今天的报纸才知道师长的大喜事,来的一路上都为您高兴,借着送伤员的由子特地来向您道喜,顺便看看有什么我能帮忙的。”徐治中听了他的话便一扫疲惫之色,笑着埋怨他,“原来你是专程来看我热闹的,如今这个战况,结婚肯定会仓促一些,也没太多可准备的,不用麻烦你。”
林副官点了点头,想了半天,他才谨慎的开口道,“刚刚在医院看见谭小姐了,她看起来没什么精神,挺累的,不知是不是病了?”徐治中听了他的话一愣,随即心烦意乱的把面前的文件推了推,“天天忙,忙得去解手的时间都要没有了,离得这么近,我都快两天没看见她了,”他焦虑不已的低声说,“央央这段时间的状态特别的不对,可我忙成这样,一直没机会和她好好谈一谈!”
林副官迟疑良久,慢条斯理的说,“师长,您回上海见到谭小姐以后就养起了乌龟,我猜这大概和诸葛孔明手里的鹅毛扇一个意思吧?感情这东西也和行军一样,欲速则不达!我想您现在这样忙,肯定有日子没喂乌龟了吧?”徐治中闻言后如梦方醒,他盯着林副官看了半天,随即懊恼不已的说,“我就不该放你出去做什么团长,让你一刻不离的待在我身边就好了!”
徐治中去医院里找到谭央时,她正闭着眼靠在椅背上。徐治中关切的问,“央央,你怎么了?”谭央没睁眼睛,很小声的说,“大概昨晚没睡好,有点儿累。”徐治中面露不忍的责怪她,“我听他们说了,昨晚做手术做到凌晨三点,你什么身体,刘法祖是什么身体,不要和他比!若是你身体就这么垮了,那就一个伤兵都救不了了!”说完,他从椅子上抱起谭央,不容置疑的说,“去我那儿歇一会儿,吃了晚饭再过来!”
由于军务繁忙,徐治中这段时间一直睡在办公室隔壁的房间,他把谭央放在床上,轻轻的盖上了被,看着谭央红肿的眼睛,徐治中俯□温和的问,“央央,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?”听了他的话,谭央慢慢睁开眼睛,“我,我没想到……”她说着,眼泪就下来了,哽咽得无法开口。徐治中看她这个样子,心有不忍,便宽慰她,“好了,不着急,等等再说,等睡醒了觉再慢慢说!”
徐治中在办公室里又忙了一个多小时,新来做副官的那个十六七岁的小孩支支吾吾的说,“有个人在军队外面等了两个小时了,一定要见您,我们说见不了,他就火了,说见不到你,他回到市里就带人把你的随园炸平!”徐治中一拍桌子,“无法无天,什么人这么放肆!”小副官吓得哆哆嗦嗦的说,“他,他,他说他姓毕!”
作者有话要说:十一要去外地参加闺蜜婚礼,节后才能更新,恳请姐妹们谅解!